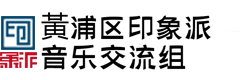这篇行文流畅有趣的文章由网友Sophie记录于2017年的7月11日,距今一年快过去了。又到了冬季时节,想必要去南岛登山的朋友也都跃跃欲试啦!不妨一起来看看Sophie的经历,也许会对你的行程带来启发或灵感哦~
(下文为Sophie的文字)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山。
这之后不久,我就递交了冰川向导申请,开始正式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冰川向导。
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在福克斯冰川的第三季里,满满是曾经的不可能。
和Phil讨论这周末要去完成怎样的任务。在他得知我们上次的钱斯勒之行并没有机会上去顶峰的时候,果断决定这周末我们就去挑战钱斯勒圆顶峰。
他想事情的时候习惯长时间沉默。凝视着桌子沉思了好一会儿大约就把行程定下来了。计划中我们周日下午搭三点的直升机上冰川,打冰川爬上峡谷侧壁,再打那儿爬上钱斯勒木屋,次日赶早从木屋出发登顶钱斯勒,然后原路折返回冰川。
运气好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搭乘最后一班直升机回镇里,不然我们便需要冒险打Suicidal Alley穿过下冰瀑回到冰川峡谷。
(Suicidal Alley长这样……走过两次之后打心眼里我不愿意再爬一次。)
我们大约讨论了一下需要的装备之后就各自准备去了。其实我要带的东西大抵都是普通游客的装备,无非就是墨镜、防晒、多几层衣服和头灯什么的。至于专业一点的登山设备,譬如六十米长绳、勾环、安全套索之类的自然是Phil准备,登山这门课我还是入门的小白,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第一日---
这日里天很晴,如果天气预报无误的话这两日里天气都还不错。直升机上了半空,打马森湖前的那片农场上空盘了个弯便往冰川峡谷飞去。塔斯曼山和库克山清晰可见,冰川也慢慢在眼前出现、放大。不一会儿,我们就在冰上的停机坪降落了。
到了冰上之后,不敢多耽搁,我们穿上了冰爪便往冰川侧壁走去。再两个小时之后太阳就要下山了,之后温度便会骤降,我们需要尽量在天黑透之前到达小木屋。保守估计,打冰川侧边走上钱斯勒木屋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冰川的变化是没办法去保守估计的。事实是,我们最后花了快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才顺利地从冰川上走下来,走到冰川同峡谷一侧相接的边界。我们在侧边的冰上徘徊了许久,眼前尽是各种大小的冰隙以及碎落的大冰块,冬日的冰川又坚硬难行,我们前后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一条相对安全的线路下了冰川。
下了冰川后卸了冰爪,大约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的陡坡。陡坡上满是碎石,我们一步步爬得小心翼翼,有一些石头上结着几厘米厚的冰,万不敢踩上去否则必定会打滑。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在冰上多耽搁的时间只能在在往后的行程赶。所以虽然爬得小心,但并不曾逗留半分——何况这是落石区。
很快我们便上了丛林。太阳也马上就下了山。夕阳给冰川染上了粉色的光,天上的云也是一团团的粉,煞是好看,然而我们也并没多看两眼,继续赶路。
又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我们走出了丛林,来到了开阔的高山草甸,又走了不多久,终于到了钱斯勒小木屋。
进了屋,卸了行李,Phil开始准备晚餐。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设了明早四点半的闹钟,早早地钻进睡袋里。
月亮早已经爬上了半空,照亮了绵延的雪山。我很快便沉沉地睡去了。
半夜里模糊中听见Kea跑来木屋玩闹,跑上屋顶蹦哒、用鸟喙咚咚咚啄着木屋的门……我喃喃地嘀咕了句,“别吵……”就又睡过去了。
---第二日---
在闹钟响起的前两分钟,我自然地睁开了眼。昨夜里让kea吵醒了三次,模模糊糊地又睡过去。
起身收拾,热了水泡茶就着椰蓉面包棒简单地解决了早餐。再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留在木屋里,中午回来再收拾。穿上了安全套索、带上头盔、冰斧、穿上皮靴、背上背包,在五点20分的时候我们推门而出。
昨夜的大风已消停了,只剩些许微风轻柔地吹着。农历十七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将世间照得透亮。不需要打开头灯就能清楚地看见眼前的路,福克斯冰川在右手边的峡谷里安静地流淌着,绵延的山头盖着雪,在月光中清晰可见,天地间一片静谧。
早上起来精神抖擞,不似昨夜里想象的那般难过。往上走的路有徐缓的坡度,一些稀疏的残雪盖在蔓延的草甸和眼前的小道上。一开始的路并不难走,大约半小时我们就到了第一个大沟壑的脚下——这是今天的第一个难关。这里的海拔大约在一千四百米左右,白雪没过脚踝打眼前铺开去。
上次来到这里还是夏天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个海拔是一点雪都没有的。沟壑的坡度有四五十度,其间填满的是大大小小的碎石,让人看着心惊。当时的向导Steve和Marius是用六十米的长绳分两次让大家沿着绳索往上爬到坡顶。
此时眼前的沟壑里盖着雪,看不见碎石。Phil观察了一下,决定不上绳索,我们直接往上爬。此时我们在雪地上已经走了一段距离,往上的行程我们都需要穿着冰爪走。
我看着眼前的陡坡,咬了下唇,暗自给自己鼓劲,不做多想便随Phil往上走。坡很陡,雪有些松,有时候一脚踩上去又滑下来,踩了几次都还在原地打滑,很是狼狈。Phil教我走雪坡的时候要像走在冰坡上一样,用靴头用力地往雪里蹬实了再往上爬。我照着他说地做,一步一步踩实了再往上走,发现很快要没了力气。
陡坡上有一段,雪层很薄,下头的雪已经结成了冰,用踩是踩不住的,只能用力将冰爪蹬进冰壁里,甩起冰斧往雪里砍去,再借助冰斧往上攀。因为对冰川太熟了,只要是冰我反而不怕,这一段很快地过去。但在往上雪更厚了一些,依旧是爬得很吃力。
Phil问我觉得怎么样?我大喘着气说还行。他说他不是问我身体上是否吃得消,而是问我心理上能否接受这个坡度。此时的我们在坡上已经走了一大段,往上看不到的顶不知道还有多远。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月亮依旧高高地挂在天上,从这里模糊可以看见远远的村庄。村里的大家都还在睡觉呢,我们俩却已经在山里头走了一个小时。天还没亮就说放弃也太说不过去了,我看着Phil说我可以的。
他于是继续往上走着,我在后面用力地跟着。力不从心,却不说停。走上几步就要停一下大口喘一下气,再紧走几步。
“嘿Sophie!” Phil回头对我说,“想一想,这可是你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山呢!是不是很兴奋?”
“是呀!” 我笑着回应,心里还是嘀咕了一句……可是真难啊……
终于我们爬上了坡顶。来不及兴奋,一想到我们走了还不到去程的一半,又蔫了下来。登这样的山对于Phil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我却要拼尽十分力才能不落下太远。
半开玩笑地,我问Phil,好不好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好了。你看这里的风景多好啊。
往峡谷的方向看过去,风景十分的开阔。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塔斯曼山,大段的冰川打峡谷往海的方向流去。
比起坡底下,现在脚下的雪更深了一些,往身后看去已经全是雪了,我们的面前还有绵延的山坡一座座。离我们想要去的钱斯勒圆顶还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距离。
“Sophie,我们是为了钱斯勒圆顶来的这里,不是为了眼前的这片风景。” Phil笑了笑不当回事,“快点,你可以的!”说完他转身往前走。
点点头,自己也跟上了。
接着的一段路几乎都是很缓的坡,虽然深深浅浅的雪踩下去又往下沉,反反复复耗去了不少力气,但也并不算太难走。雪地上干净得没有任何别的足迹,有一些地方的雪已经有点冰化了,才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有一些地方的雪踩上去粉粉、软软的,特别舒服。这是否就是Tak口中的粉雪,我自己默默地在想。
七点出头的时候,月亮还是老高的。从身侧照来,映着自己的身影在雪地上。雪地上反射着星星点点的光亮,仔细看,原来是雪上结着的冰晶。这些冰晶反射着月光,就如天上的星星一般发着光。自己的身影在雪地上铺开的点点光亮中移动着,恍惚间有种错觉自己是游走在浩瀚的宇宙中,在无限的星河里。
有一度我们都被眼前的风景迷住了。月光下的一切是那么的静谧而美好,
“你听见了吗?” Phil站在月光里,转身忽然问。
“听见什么?”我疑惑。
“寂静的声音。”
海拔一千六的雪地上,除了明月光和我们,万物皆休。我们闭上眼睛,仔细地聆听着这片天地间的寂静。
不是。是有声音的。
有风的声音。远远的吹在峡谷的那一侧是模糊不清的背景音,还有近在耳旁微弱的风吟。
有雪的声音。小雪团让微风一吹,打雪坡上扬开,在雪地上打滚是沙沙沙细弱的声音。
我们已经可以看的见福克斯冰川的源头。又走了不一会儿,我们看到了一面小旗。Phil说那是直升机观光公司在雪地上的停机坪。果然看到小旗的附近是各种杂乱的脚印。
“你看,我们自己爬上来可不是省了几百刀呢!” 直升机观光一趟两三百刀,在雪地上的时间也不过五到十分钟。哪来的及听见雪球在地上滚的声音,也没机会看见月光下雪地上的星海……
“往前的那座高峰,看见了吗?” Phil指着遥远的前方,“那座高峰的脚下就是PioneerHut了。”
Pioneer Hut早已成了心里默默立下的flag。上次Phil和Jules他们一起周末里从钱斯勒小木屋出发跑去那里,花了整整14个小时的时间,在半夜三点才回到了冰川小镇。那个木屋就在雪地里,其下是深沟。曾经有没经验的外国游客租了直升机降落到木屋旁的停机坪,以为走两步就到了。结果第二天直升机过去接他们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在雪地里呆了一整夜,因为根本不敢走过那个深沟,虽然木屋就在眼前。
公司里的一些向导们在过去的夏天里都去走过了。对体能是一个大考验。我知道现下的我还办不到,但我可以预见未来的某天我也会坐在木屋外头的甲板上,泡着茶看着夕阳打塔斯曼海沉下去。
我们接着往前走。又走了半个小时到了很开阔的一片雪地上,Phil说那里应该就是Alf Glacier。上次来这里还是一大片的冰川,而今盖上了茫茫的白雪竟有点认不出来了。
我有点雀跃、也有点紧张。上次我们就是走到那片冰川的边缘最后折返的,当时因为天气耽搁了半天,待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太阳照在冰川往上的那片雪坡,Marius和Steve看过了之后说太危险了,我们便没再往上走。
此时山那头已经泛起了光亮,太阳马上要升起来了。月亮也往西天沉下,沉没在橙的粉色光晕中。东边的天空和山头一起白亮起来了。
Phil说打Alf Glacier开始我们要马不停蹄地往前走,不可逗留。那个我们上次却步的山沟,就是这段行程最危险的一部分。在这里,最有可能发生雪崩,我们可以看见陡坡上已经滚下来的无数的雪球,都停落在坡下。虽然现在太阳还没有照在这片雪上,但是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我没料到的是,这片雪域不只危险,而且甚为难爬。这里的雪越来越深了,浅一点的也有没膝高,踩一脚下去不停地往下陷,再抬起一只脚时原本踩在雪上的那只脚更吃重会又陷进去一些。有一些地方的雪甚至深到了大腿,拔起来都吃劲。走每一步都是在做高抬腿,很快地我就发现自己快没有力气了。
Phil还是在前面走着,我们此时在彼此间系上了长绳,保持着七八米左右的距离。我不能停,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拖累Phil的步伐。可是我又不得不走几步停下来大喘口气再继续走,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的呼吸中开始带着哭腔。
我累极的时候就会哭。印象里这是这辈子第三次,不过没有哭出声。
可以看见Phil也走得很吃力。他比我更重一些,而且每一脚都踩的踏实,也陷进去更深一些。他让我踩着他走过的足迹走,会省力一些。但他的步子太大了,我没办法跟着踩,只能是憋着口气一步一步埋头走着。
我看着走在前面的Phil,沉重的步伐,硕大的背包,弓着背埋头走着,忽然让我想起了电影里看到的那些挑战六七千米以上高峰的登山客们。心里甚是敬畏。我们这不到两千米海拔的雪山就已经让我如此挣扎,心里必得填满怎样坚定的意念才能坚持走完数千米的高峰呢。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月亮也埋进了浓雾般的光晕间不见了。塔斯曼山和库克山就在眼前,山头染上了金色的阳光。
我已经放弃想要放弃的念头了。雪山上的温度应该有零下,可是我却浑身发着热。手套因为反复扎在雪里,已经几乎湿透了。冰斧上的绳套竟然冻住了,定了型。打开水壶想要喝水,却发现水壶里也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手机在刚爬上第一个陡坡的时候就已经因为太冷自动关机了。
此时我们已经走在阳光里,天彻底的亮透了。走在月光下的画面仿若是隔了很久以前的记忆。
Phil指了指前方,说那就是Chancellor Dome了。我对距离已经没有了概念,反正拖着步子一直走下去总会到的。再往前走一点,Phil看了好一会儿决定不过去了。因为前几日山顶的大雪,堆成了陡崖,横亘在眼前。你不知道踩下去下面是实的山坡还是雪堆罢了。若只是崖上耸出的雪堆,踩下去怕是连人带雪都会往崖下坠。
他指了指我们身边的一个高耸的石崖,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高峰了。”
这个石崖就叫Rock Summit,是和Chancellor Dome一个海拔的高地。一听这里就是终点,我整个来劲了,跟着Phil穿着冰爪就往崖上爬。相比起走雪地,爬山这种小事简直是太容易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爬到了崖顶。很小块的一片雪堆在崖顶上,我不作二想,卸了背包一屁股就坐上去。
终于到顶了……
心里一放松,就干嚎了起来。
我想起Phil说过,对于登山客来讲,登山是戒不掉的瘾。你明知道那里有困难,那里有危险,明明历经了千难万难到达了山峰,一路骂骂咧咧说再不来第二次了,但是等从山顶上回来之后,很快又回去挑战下一座山。
我不知道我是否也会染上这样的瘾。
从Rock Summit下来之后我们又花了六个小时,才下到了冰川上。最后搭了四点半的飞机飞回了镇里。
回家之后在家里的床上躺平了十五个小时。前一日的经历仿若是梦一场。
翻看着那日里的照片,心里止不住地想,这真的不是一场梦吗?
如果再来一次,你还会去吗?明知道那种挣扎与疲累,明知道那种力不从心。
会的吧。
为了清晨的风吟,为了月下的雪地,为了照在雪山上的金光。
就算哭过、怨过、几次想要放弃又怎样?
只要最后到达了那座顶峰,看到了想要的风景。
就算曾经懦弱、挣扎,又怎样。
作者介绍
Sophie Chen,陈酥肥,福建漳州人
现居于新西兰福克斯冰川小镇三年有余
爱喝酒、爱家人、爱大自然
固执而任性,高冷又闷骚
独处时容易面瘫,也常会把自己逗乐
是个活得不大痛快的逗比
扫下面二维码关注她的个人号: